优美散文 2022-01-28 03:36:13 人气:2565
老房子给人一种很微妙的感觉,那些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值得欣赏。下面是短篇文章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供大家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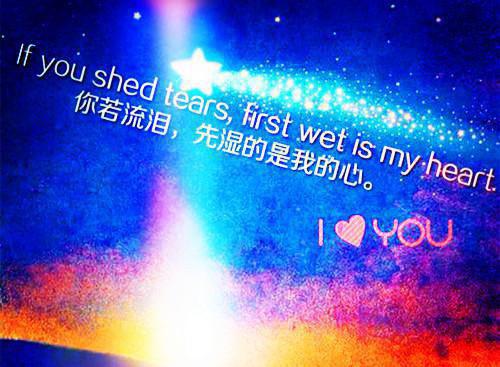
作者:夏荷依旧
旧城改造过了有好几年了,可脑子中总时不时浮现老房子的影子,那院子里的香袍树,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在夏日里静静地开着灿烂绚丽的红红绿绿的花儿,在夜里散发出醉人的香气,叫人闻了就会有种被陶醉的感觉。
老房子里的母亲和我养的两条叫小五和妞妞的狗狗是这里的主角了,每天母亲打扫着老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上街买菜做饭,两条小狗相互嬉皮着,你咬我的尾巴我咬你的脚脚,有时会突然闯到门缝墙角去扑抓老鼠什么的,还真有几次抓到了老鼠呢。到中午母亲就会到弄堂口来接我下班,而每次我刚到门前就会被从家摇着尾巴猛扑而来的两条小狗狗缠着叫你迈不动脚,还是母亲手拿扇子扑打着它们才让我得以解围。
老房子夏天的晚上是很凉爽的,反正自我做了人父有了孩子以后的夜里,母亲会时不时地给孩子盖盖被子,怕夜里被冷到。小狗狗则各自睡在大门的两侧,皎皎的月光透过天井照在大厅里,墙角的昆虫们也各自唱着歌儿,晚风吹着花香一阵阵钻过窗子的缝隙飘进熟睡的人们的心扉,——————那种和谐是一般人无法可以理会的。
现在每每走到城里有老房子的地方女儿和我总会停下步子,细细打量着,仿佛就像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也难怪女儿时常赖着要我给她买条狗狗,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一种想带着女儿牵着狗狗静静地享受着皎皎月光下的那叫也叫不来的花草的香味,这种看似简单却一生难求的完美和谐何时才能回来哟?
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连队的老房子作者:凤舞九天
我出生在60年代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人们的住房都是七八家住一排,房子都是连队领导组织职工利用午休时间组织大伙盖起来的,那时职工大突击,脱土坯、砍些杨树或柳树做檩子、椽子,红柳扎成排子,连队的大马车从地里拉回整捆整捆的麦草匀匀实实铺在顶上,上面再撒一层薄土,最后用泥抹子把泥巴和粉碎的麦草搅拌均匀抹的平平光光的,有几个大太阳就晒的差不多了,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搬进新居的职工一家可以分到一间半,当时最高兴的就是住新房了,搬进新房后,大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利用休息时间脱土坯,在自家住房正对面盖起简易的棚子,用来装一些杂物或者是到了夏天就在棚子里做饭,棚子盖得高低不一,大小不一,有的结实有的简易,在棚子了做饭的时间可持续7个多月,主要是烧一些棉秆和干树枝,要不就是带着孩子去戈壁滩拾回梭梭柴,整齐地码在自家棚子后面,谁家的柴堆大,就显得谁家人很勤快,很能干,至少当时我们这些孩子是这样认为的。
住房里少了些许的烟熏火燎,家什农具,空间就大了许多,稍稍勤快些讲究些的女人会唆使自家爷们去连队保管员那里讨要些石灰,利用中午时间把墙刷的雪白,量好高度,用细细的铁丝按照经纬在铁丝上固定牢实,打些浆糊,刷在白纸上,一张挨一张糊在铁丝上,等浆糊干了,平展展的显得房子里亮堂堂的,房子的干净整洁也引来不少孩子们的观望,也会引来女人们羡妒的目光。
那个时候的职工家里最少都是三个孩子,多的七八个,到了下午,连队里一排排的住房前真的热闹非常,放学的孩子们嘻打笑闹,玩打仗的、抓骨子的、踢沙包的、跳房的,推铁环的,藏老猫的,撵的原本悠闲自得,四处啄食的鸡群惊叫惶跳,有几只甚至惊吓的飞到了棚子顶上,引来孩子们一阵阵无忌的开怀大笑。
当袅袅的炊烟升起在黄昏的雾霭里,就传出母亲在呼唤玩闹逐远的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听吧,那口音是南腔北调,呼唤的声音也是此长彼消,连队的职工原本就来自全国各地,一排房子居住的人们更是天南地北来的,一直到天黑透,这些闹吵声才逐渐消失,再过一阵,就只能看到人影透过窗帘在模糊的灯影里晃来动去去。
现如今连队里人们的住房大多是砖混结构,许多职工已经在团部买了三室一厅的楼房,可是我还是很留恋那时的快乐,不论在何处遇到曾在一排房子住过的旧邻,总是感觉很开心和激动,在对同伴介绍时会自豪地说:我们小时候住一排房子。
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老房子离开故乡十多年了,常常会在梦里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回到魂牵梦萦的老房子里。那里,留下我们全家人曾经的点点滴滴;那里,生长着我们全家的欢声笑语,那是我始终无法忘怀的牵挂。
我家的老房子,坐落在我们村的河对面,一座高大的半圆形山拥抱着我们家族曾经的十户人。那里山青水绣,空气清新,风景怡人。每到春天,草木发芽,房前屋后的老杏树,开满了淡粉色的花朵,微风轻拂,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引来无数蜜蜂嗡嗡地採蜜,树下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嬉闹,惊得花瓣纷纷扬扬飘落一地。那些泥墙,青瓦,木门,都掩隐在花海里,伴着袅袅的炊烟,这便是我记忆中故乡那幅迷人的乡村图画。
春节回家后,总想去看看老房子。搬到城里后老房子就一直空着,如今那里的年轻人都已搬到干净整洁的小康村去住了,只有三爹老俩口和小叔老俩口在那里住了。弟开车带我去老家看望几位老人。
走进村子,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小河,熟悉的山路,熟悉的草木。车停在小路口,那条我曾经走了二十多年的小路,长满了草,路两旁的地里,到处都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松树,让人感到有一种无比清爽的自然美。沿着小路来到老房子前,大门外,长满了野草,洁白的积雪上没有任何的印记,一把铁锁孤独地守着门。我们没有进去,站在高处向院子里张望。想起曾经的小院子是那么的干净温馨,那时院子里有一块菜地,母亲会种上白菜,萝卜,菠菜等各种蔬菜,还会在边上种上八瓣梅,指甲花,九月菊等各种花,夏天一片绿油油,秋天五颜六色满院花香,多么的令人陶醉。而如今的院子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各种杂草,挡的连人也进不去,显得是那么的苍老而荒凉。院子上角母亲栽的那棵筷子长的小云杉,已经高出房顶许多,虽然多年未修剪,但仍是那么的苍翠娇健,枝叶茂盛,样子如同一座尖顶的塔静静地守候着老房子。
曾经的厨房,房顶和后墙都已塌了个大洞,似乎大雨随时都会冲倒,看着让人有些揪心。母亲曾在这间厨房里忙碌劳做了大半辈子。虽然是土房子,但母亲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东西永远摆放的有条不紊,水泥锅台擦得油光明亮。那时候虽然穷,但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正睡的香,而母亲就会悄悄起来去厨房,做我们姊妹几个上学要带的玉米窝窝或黑面饼子,然后再做一大锅洋芋面,叫我们起床吃。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看母亲做的热气腾腾的饭,浑身暖融融的。吃饱了,母亲会把烙好的饼子分给我们带着去上学。我们踏着微亮的晨光哼着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些记忆是多么的清晰,多么的深刻。苍桑的寒风,拂走一串青春的想念,回首,仍是甜蜜。而那些闲置的篱笆,影子和墙,无言,无语的静默着。
风干的昨日,看往事,在如水的诗行里蹁跹,时光,悄然从指间溜走,老房子,留下了我们全家无数的故事与酸甜苦辣。曾记得,我们小时候挤在热乎乎的光席炕上,听妈妈讲故事,当我们慢慢进入梦乡,而母亲总是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或做鞋子。有时一觉醒来睁开惺忪的眼晴,看见母亲仍低头凑在油灯下,手上下挥线的身影。曾记得,每年快过年时,我们都会和母亲用旧报纸糊墙,每年糊一层新的,而糊好报纸后,母亲总会用她灵巧的双手,把红纸剪成各种大大的花朵贴在墙上,还会剪各种各样彩色的窗花贴在木格子的白纸窗户上,既喜庆又好看,增添了许多过年的新气象。曾记得,每到大年初一,家族的兄弟姐妹们都挨家挨户的拜年,那是对长辈的尊敬,也是为我们每人能分到一块糖或一个核桃,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喜悦时光。一大早孩子们笑嘻嘻地跪一大片,屋里跪不下就跪在院子里,拜完后父亲总是慈祥地微笑着把每一块糖放到孩子们的手上,孩子们那种开心与幸福是无以言表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总是给人温暖,令人思念,那是岁月留下的瓣瓣心香,在记忆里永恒,在时光里安祥。
现在的正房是十多年前新盖的,还能记得盖房子时我们全家和村里人忙碌的情景。盖房子用的石头,沙子,都是我们全家人用小木车一车一车从河沟里推回来的。老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有父母亲手劳做的印记,那是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创建的家园,是父母的自豪。那里是父母的根,也是我们的根,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凭借一抹温馨的乡土气息,让一颗疲惫的心回归故里,找到那一种久违的感动和温暖。
三爹送我们出门,指着他房后的一块空地笑着对弟说:“这是我的坟地,将来我要睡在这里,我要守住这个老地方,不能丢。”看得出三爹是多么喜爱和留恋老地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他当然舍不得离开,这种思乡情结,也许年轻人是无法理解与感受的。
要走了,还不舍得离去,站在门前到处张望。门前的地边上,是我曾经和父亲,姐姐亲手栽的几棵一尺多高的小松树,如今已是十多米高的大树了,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也不再年轻,但这些青翠挺拔的松树,迎着风,迎着雨,顶着雪,如同饱经风霜的老人安详站在那里守望着家园。我用手机拍了几张老房子的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不只是存在我的手机里,而是永远地存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动,让我怀念。
老房子,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永远的家,永远的记忆,永远的牵挂,永远的想念。首望,心中带着千万的不舍离开老房子。我的老房子,再见。
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老房子的风景我住在市郊一处五层楼的老房子里,远离市井的喧嚣。老房子有些年代了,斑博的墙壁,厚实的砖块总让人想起过去久远的日子。我总喜欢有沉淀的东西。城市的高楼一幢幢拔地而起,我却不曾有向往之意。那样的新房总让人不踏实。虽然房产广告中关于漂亮的江景、便利的交通等诉求撩拨着无数人的神经。我一直知道老房子一旦消失,那些年代的气息就永远不复存在了。所以住在有年份的房子里一直很安然自得,甚至希望不要拆除。
过去周围有一些田园景色。可以看到大片的田地,闻到地里青菜的清香。傍晚散步时稍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满池的荷花。夏季赏荷,秋季听雨。日子无声无息过去,却始终伴着大自然的丰盛气息。
离开几年再次回到老房子,绿油油的田地已不见了,大片的现代工业厂房生命力勃发地矗立在窗外不远处。连那一片荷塘也不复存在。小楼还是那样子,静静地,立在小路边。家家户户的窗子仍然没有安装防盗网。没有不法分子惊扰这里的居民,像鸟笼子似的防盗网有太多的视线束缚和不良联想。没有铁槛杆的窗台可以更加随性地呼吐大自然的气息。
尽管少了田园风情的窗景,可窗外的几株梧桐树和意杨仍然枝节繁茂,无拘无束地生长着。我的窗台还多了几盆花花草草。茉莉花、小枝玫瑰在季节里各自美美地绽放着。在冬季里叶子被剪得只剩下枝枝桠桠,可一到春天,只一夜的功夫又奇迹般地长满绿叶。植物们简单又顽强的生命在我的窗台兀自傲立着,悄然无声,又互不惊搅。却给了我许多的惊喜与慨叹。
小鸟枝头春意闹。当清晨被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惊醒时春天的气息已浓浓将我包围。窗外的那几株梧桐和意杨成了各色鸟儿们安居之地。密密的枝叶间隐隐可见鸟儿停落枝头的身影,有时还可以看到飞鸟嘴中衔着小树枝飞进树桠间,不几日,树桠间就有一个黑色的小鸟窝。
鸟的种类很多,喜鹊、灰喜鹊、麻雀、布谷鸟、燕子等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鸟,各种鸟叫声也是不同的。除了布谷鸟的叫声我至今也没有分清楚其它鸟叫声。
每每清晨,似乎还恍惚在梦中,小鸟们的鸣叫声就已进入我的梦中,我总隐约觉得自己似乎睡在山林里,空旷无人,只有花香鸟鸣。当我醒来细听那鸟鸣声,好像所有的鸟儿们都聚在一起开会,它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热闹不已。这是早上我听到的最好听的自然音乐。等到我一起床,走到窗台细听却听不到众多的鸟叫声,似乎开完会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了。只偶尔看到天空中飞过几只小鸟,间或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
傍晚吃完晚饭到楼顶的天台上漫步时又听到林间传来各种各样鸟叫声,那热闹劲儿跟清晨一样的。倦鸟归巢,想必它们忙碌了一天回到林间各自分享各自的亲历和收获吧。
下雨天里早上的梦总是被哗啦的雨声惊醒。朦胧间细听,却听不到一丝鸟叫声。今年的雨不似往年,总是哗啦啦,一下一整天。有人说鼠年水多。在下雨天里除了雨打绿叶的声音,什么声响都听不到。房间里也很寂静。我坐在靠南窗的书桌旁看书,通常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天。厨房里偶尔传来父亲切菜的嚓嚓声,油锅里炸油的声音,那是最喧闹的地方。倦了就趴在窗台看遮阳篷上滴落下来的或粗或细的雨线。眼睛也会往梧桐树叶间搜寻,找了半天才发现一只小鸟立在枝头,缩着脑袋,无声无息地淋着雨。小鸟不怕冷?会不会淋感冒?心升疑惑又不得解。
有时也会在下雨的午后弹筝。水波样的声音在木头的纹理间荡漾着。满屋子筝声在墙壁、书架间和木柜子中回荡着。古代弹琴或弹筝讲求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意境。尽管筝声已飘出窗外,飘到了林子里,却不曾引来鸟儿们的和鸣。而在晴日里,只要筝声响起,连蝴蝶都会在窗台的花花草草间流连。不过雨天耳边伴着雨声,也觉曼妙。
在夜晚的天台上可以看到远方高低错落的现代楼群,灯火闪烁,一片眩烂。视线无遮无拦,一片通阔。每到月中的夜晚,也可以看到一轮明月和一些星星,在空旷简洁的深蓝色天空中。若居于闹市,想看到一片完整的天空都不能,那里全是高楼。不过在窗台看到的月亮却更多是月上柳梢的景向。坐在靠窗的电脑旁敲字,无意中瞟一眼窗外,竟发现树叶间的一轮满月,才陡然记起,又是月中旬了。推开纱窗竟闻到了茉莉花香,浅淡的喜悦在心头荡漾着。
心中却窃窃地念叨着,不要拆掉这老房子才好,哪怕它破落点、陈旧点、窄小点,哪怕它只静静地立在城市的一隅,无法与那些贴着漂亮马塞克的现代高楼相媲美。可它有年代久远的故事,有丰富的情怀,还有重要的一点,每日清晨在鸟儿们的鸣叫中惊醒的片刻似乎听到了山泉流淌的声音,似乎听到了山谷的回声,这样的错觉,让人沉迷……
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老房子和童年看到老房子的照片,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些事情来。
前几日去盐官,看到以前繁华的宓家湾和居家弄一带,怎么整的象日本鬼子进过村似的,一片断壁残垣,荒凉狼藉。一路过去,也没遇上什么人。路两边的电线杆证明,这电线杆二边以前是房子和街面,证明着以往的繁华。听说去年这里还上吊死过一个人,有点毛骨悚然。如果遇上阴雨天,这里真不敢走。
但是,记得这条路一直是伴随我长大的。
很小的时候,奶奶牵我的手经常去街上文化宫看戏文或者和父母去看电影。一路上的人家差不多奶奶父母都认识,一路招呼过去聊天过去,感觉路特别漫长。特别是奶奶,碰到老朋友了,站在路边一聊就是n久,有时偷偷扯奶奶衣角,奶奶才会依依不舍地和她们告别。
宓家湾那边有一些老房子,后来陆续都拆了。有一家拆的只剩一个外围墙和门档子,放学路过时,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有时站在门口,叫她一声“祖奶奶”,她就会笑得象花一样。还有一家姓陈的,以前是大户人家,陈奶奶不会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长大后在上海安家落户,好象是做警察的。陈奶奶一个人住一个大宅子,前面的大楼房让国家买了去,做粮管所仓库了,就住后面那一排房。楼房我偷偷去看了看,黑黑的,有点吓人,楼梯走到一半就下了,不敢上去看。
就是后面一排房子也挺大,侧门进去一个天井,有一棵高大的树(好象也是榉树),种了一些雨后兰,凤仙花,鸡冠花和一盆朝天椒。穿过走廊一个小会客厅,东面一个小天井和一扇小门,插着门栓。小客厅南面就是连着大楼房。
奶奶和我常去陈家奶奶家玩,那里经常有好几个奶奶过来玩,差不多都是从前的千金小姐或少奶奶吧,那时都已白发苍苍了。陈家奶奶不是小脚,我称为“大脚奶奶”,她家还租了一户人家,那个奶奶是小脚,谓“小脚奶奶”(一次洗脚,我不小心看到,脚趾头都在脚底下面了,好可怜),都是民国前后出生的吧,所以大户人家也有小脚,也有大脚的。陈家奶奶从前是少奶奶,生活一点儿也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都是别人伺侯过来的,因此她女儿托了镇上一个女干部,经常来照顾她,有时睡那儿。
那时候,真的挺好笑,和奶奶看完丛珊和朱时茂演的《牧马人》,一群昔日的千金小姐和少奶奶就谈剧情谈的兴高采烈的。每次去的流程,差不多就是:我和奶奶先搬个凳子坐下,然后问问我学习,夸我一下,拿出点好吃的,大伙儿开始东家长西家短的聊一阵,起先我听她们聊,听不懂就自已屋前屋后的瞎玩,或者自个儿在那大青砖上玩跳房子,后来,小脚奶奶家的小女孩杨倩有小人书,就去借《聊斋》的《小翠》《婴宁》什么的看,特喜欢。
那个老房子对我印象特别深,有时经过的时候,有种想进去再看看的念头,不过现在听说也拆掉了,给了上海女儿三套商品房。老房子不是说不拆的嘛。
那是人家的老房子。
咱自家的老房子,和老房子里的故事,多了去了。从小由奶奶带大,整天听她唠叨从前的事。什么太祖父从哪里搬来,这里造几进房,有多少地,一直讲到爷爷和她,还有爷爷的二奶和他私奔什么的,甚至咱花家埭日本人来过,逃难到江南什么的。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想起,我为什么没有把它记下来,以后找人写成小说,也好留个念想。黄家的辉煌有时被父亲偶而提起,父亲生下来的时候,咱家应该败落了好几年了吧。听奶奶说,爷爷和二奶私奔了以后一次来看她,就生下了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应该没有经历过昔日辉煌,只有北京的大伯父经历过,大伯父比我父亲大十五岁。
现在那块曾经砌在墙角的“仁德堂黄”石头,上面的字被我父亲用红漆描了描,放在门口,算是黄家从前辉煌历史的纪念吧。
这篇优美散文《描写老房子的抒情散文欣赏》还未收到评论